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(b��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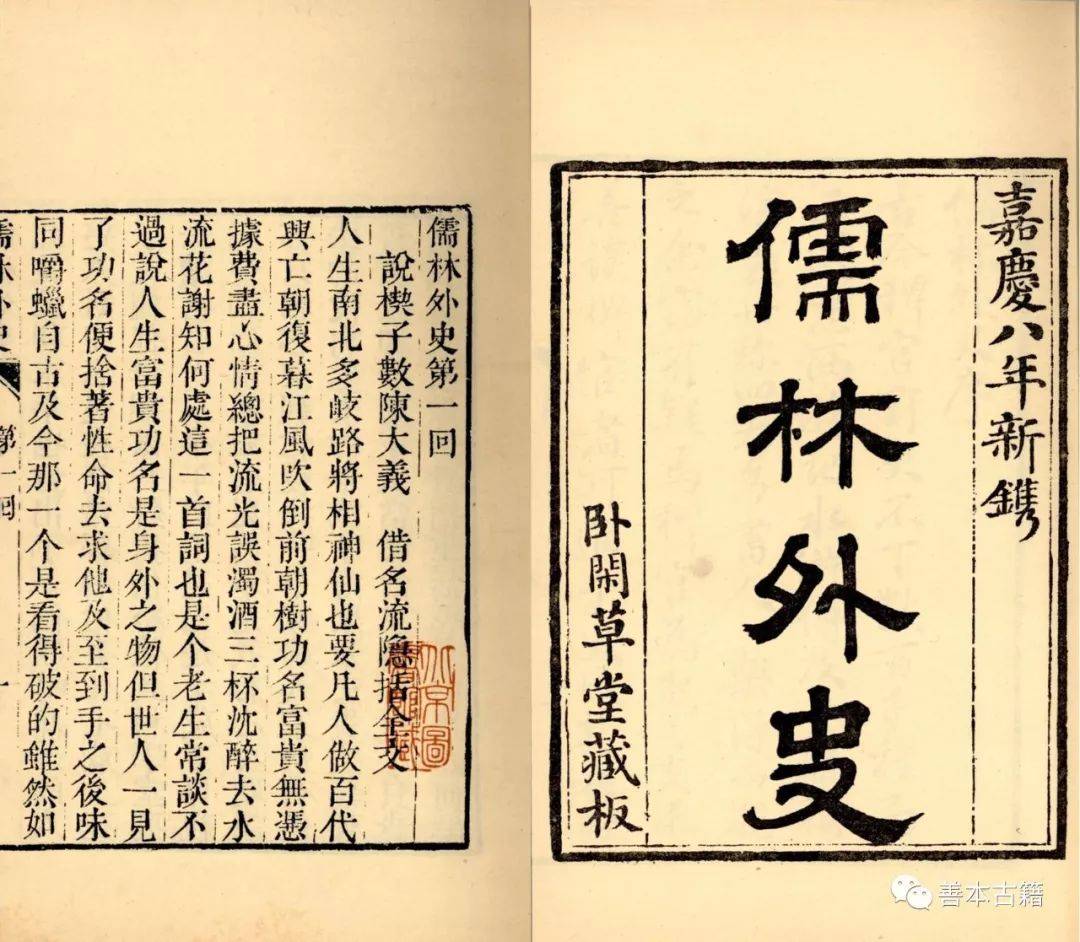
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Ѹ��Թ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Ă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Ѹ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f��ָ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f��ָ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Փ��Ӗ(x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۹⡱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ҿ���Ҫԓָ���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Ļ����ל\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N(y��n)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Ʒ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)�ص��S����ζ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}���ڽ�qȻ���о��ߵ�Ҫ��(w��)֮һ���nj��@��С�f���Ļ��N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ԏ����U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
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ķ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ᵽ�˕��ąǾ������ѳ̕x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F�O��ʿ��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Ѹ�f�����C(j��)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֡������Ї�С�fʷ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Ѹ���ìF(xi��n)�ɵġ����֡����á�ʿ�֡�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õ����Ĵ_���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ǏV���ġ�ʿ�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ǪM�x�ġ����֡���Ū���@�c(di��n)���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ȥ�ǘ���ҕҰ�������ڪM�x�����ֺ����˼�뷶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y(t��ng)˼��ăɴ�֧�����ڝh�Ժ���Ї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o)���á�����Խ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Þ���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Ó����ɫ�������ϱ˴���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H�υs�ֻ����a(b��)����f(xi��)�{(di��o)���ɞ�v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ɵăɴ���֧�����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˼��Ѭ�����γɵ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ڳ��˺����[�Ќ�(sh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ą��c�ͳ�Խ���ʷ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`��������茑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漰�������ɼҵ�˼�롣
����ɼҶ���ҕʿ�����`���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ҕ���˂�������(qi��ng)�{(di��o)���ˌ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(w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_�����w�ăr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ҕ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룬�����ڳ�������д_�����w�ărֵ��
���w�Ϸքe�c�塢��˼���МYԴ�P(gu��n)ϵ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ʿ�ɴ�֧����ʿ�֞��茑���ĵġ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Ҍ��˴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Ȼ�s̎��ǰ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ע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ҕ��16��ǰ�Ұl(f��)���ˡ��Ǿ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cκ�x�L(f��ng)�ȡ�������˅Ǿ�������κ�x��ʿ��κ�x�L(f��ng)��Ӱ푵Ŀ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w���ў�W(xu��)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ͬ��ѭ��܉�E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һ���J(r��n)�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(b��)��˼�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Щ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ʿ��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l(f��)��ʿ����ʿ���Ե��Ļ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͚vʷ�YԴ�����ȰѶ��߷��_���U����Ȼ���ٿ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���Ć��}�ǹ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đ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nj�ʿ����˸�Ʒ�е�ԇ��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г�̎�đB(t��i)�Ȟ����ģ���С�f��ӽ���(g��u)��һ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ȵĽY(ji��)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ͼ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־��ڌ��ȽY(ji��)��(g��u)�ăɂ�(c��)���γ��r���Č�����ֻ�ЏČ��H�c�����q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̽�y��Ʒ��˼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B���^ȥ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ע��ö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(y��n)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Ŭ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C�ذ��գ������Ąt��(c��)�����U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N(y��n)��
��ʿָ������ҌW(xu��)�f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⽨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ҌW(xu��)�f���v����һ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Ч��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ǃ�(n��i)��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顰��(n��i)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Ҳ�ͬ�ڵ��ҡ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Ҫ��ɫ���v�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˽�(j��ng)���@��Ŀ�����ǾͲ��Ǽ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x�_���˂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ģ��Ǿ�ʧȥ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x��׃�ɼ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�ƶ����˹���ȡʿ�Ŀ��e�ƶ���ͨ�^�˹ɿ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ɞ��v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;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ٵ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Ķ�ʹ��ʿ�ij��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˵Ĺ������غ�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f��)�s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һ��ʧȥ�����г�̎����ԭ�t���Ǿ͕��ݳ���Ц���ɑz���ɱɵ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Ϭ���ĹP�h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Ҿ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̖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H�ϗ����Ȅ������x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u�ļ��壬�����S�ʵć�(y��n)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݅Ͷ�ԇ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Ц�����ԝM�ѱ����ĺ��I��Ц����ʾ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Y(ji��)��(g��u)�зe�������һ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ڰ˹ɿ��e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R���ǘӱ���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�庮��ʿ����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ʧȥ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ț]�С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·�ƽ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뱧ؓ(f��)���֛]�гГ�(d��n)�ᳫ�Y�����x��؟(z��)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]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n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־ʿ��ѣ�׃��Ψ�˹��ǸQΨ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⫬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B(t��i)��ª����
�v���˂����µ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l(f��)չ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ij�N͑׃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һ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V�I(l��ng)�Ľy(t��ng)�z�����˵�һ�ж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峣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ҡ��ߵ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ʧ���ҡ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ˑZ��Ů���^ʳ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@�͞����D��Ó���g���`�ĵ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һ�l�M(j��n)����˼��Ŀp϶���mȻ�ĸ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ԭʼ��W(xu��)��ԭʼ�˵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팦����^���Ե���W(xu��)�̗l��
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ɫɫ�ļ������c֮�����գ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Џ���ʿ���Ļ����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(b��)���Ļ����в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׃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
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ǘ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顰ʿ־�ڵ�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ng)��(d��ng)�ԡ������ijГ�(d��n)���Ծӣ��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ֵȡ�����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)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ڳ��˵Ć��}�ϣ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]�đ�(y��ng)�ǵ��ĵ�ʧ�����ǂ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nؚ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̎�Ĵ�(ji��)����(y��ng)��(d��ng)�Ե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Ը����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ĸ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
�����е��tҊ���o���t�[�����е�ؚ���v�ɣ��uҲ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uҲ��
����Փ�Z•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Ҋ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߀���[���dz�߀��̎����ȡ���F߀����ؚ�v�����Ђ�����ԭ�t����ȡ�Q�ڰ��Ƿ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ܷ��е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֮̎���ɞ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ԭ�t���ɞ顰���塱�������µĜ�(zh��n)�t�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ᗉԭ�tһζȥ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Ǿ͕��ɞ���塣
�������ă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•�M���ϡ�����һ��(ji��)�f��
���Ӊ|��Ի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Ի������־����Ի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־����Ի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·��ص��O(sh��)Ӌһ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ij�֮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־���ֽB�⡱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˽B��ʿ��־֮����
��ʿ�܉�Փ�F�_(d��)���Ե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@����Ȼ�ڙ�(qu��n)��֮�Ᵽ��һ�N��(d��)���˸����l(f��)չ��һ�N���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�ٵ����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ƌ�(d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ڄݵ��^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(li��n)ϵ�Ŵ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t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Y�t��ʿ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ɞ�һ�N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ʹ�ܡ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λ����Ұ�o�z�t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Ę�(bi��o)־��Ҳ�Ǿ���ʥ���ı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t����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bi��o)־�����κ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34��35�ؼ��Ќ���ʥ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ٴ�����f��־���]��Ҋ���Y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o��߀�ҡ�����34�ؽY(ji��)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͢�е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ߐ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߹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ɻ����ֺ��f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耳���էһ�����@�Y(ji��)�Z�nj���͢����o��(li��n)ϵ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͢�е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ߡ�ؚ���v�ɐuҲ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ng)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˼��(j��)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ι��f��־�sҪ�o�߹ٶ�څ�[�ݣ��@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ڡ���o����֮�r�����߲Ų�ȡ�ĝ����Ԑۡ����c��ͬ͢�����۵�ѽ�����ߌ��f��־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ì�^��ֱָ��߮�(d��ng)�ֵģ��ڡ���ϯη���֪z���ĕr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ò��[����¶���W�q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ַ��ͷ��Z�����I�S��
�ҿ��f�B�⑪(y��ng)���ٵ���͢�r���ʵۺ͙�(qu��n)��̫������һϵ�б��ݣ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á����F�ăx�ơ��e�г�Ҋ��䣬���DZ����Ҋ�H�Դ�ԃ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г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(qu��n)��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ҕ�����Z�f�B�⣺������֮�T�����Ԟ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֪���@�dz��Й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�ͽY(ji��)�ɵ���Ҫ��ʽ��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֮ͽ�u��Ͷ��Ω�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s��Ȼ�ܽ^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@һ�ܽ^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˻�ǰ������߀�Ǻ����qԥ���@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ĵ�Ы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c갂}С�˞��飬���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˳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ʧ����Ԓ�f�ú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أ����ڈԳֳ�̎���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фe�o�x����ֻ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n߀ɽ������
�ʵ������mȻ�J(r��n)���f�B�⡰�W(xu��)���Y����s ?w��i){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ʿ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Q���E���ҳ����ڟo�˷��ȡ������ǽ�ּ������߀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ì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Ҋ�ģ���ȻҪ��ر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ʿ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ȡ����ֺα�ɷ�н��µظ�ʲô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ٴ������Ҋ�@ֻ��һ�N�b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ݣ��nj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Ū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t���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f�B��x���ͷ���;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á������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|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՚����R�ź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֪z���B���[�s�����¶����(d��o)���t����Ұ�����Σ�C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Σ�C(j��)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͢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^�@һ������Ը�ġ����ҕ�족���f�B���ȥ����Q���ѹو��İ�������ҕ��ຣ���Bҹ�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㵽�@�K�J�n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�ȥ��һ߅���һ߅�x�����䌑�ġ�Ԋ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λ��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�ʿ�c��ʿ�Ľ��羀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c��ʿ�����以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t��(d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(d��)�t���(j��)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һЩ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Ǐ���ҵ��@�l����(d��)�ơ�֮·���ҵ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֮�T���ڰ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·�ƽ���¶��ܵ����۵ĕr����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܌W(xu��)���a(b��)�䣬����һ�N��Ó����͵����@���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˻��a(b��)���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߀�f�B�Ᵽ������̎�t��ʧ�����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^�ߵ���ʿ�Ļh�ʸ�ǰ��ֹ�˲������ҵ�˼��ѪҺ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x��(li��n)ϵ���ǶY�������ӌ��Y�f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ְѶY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o)���ƶ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ı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ʿ���@�Nԭʼ�Ļ������ܣ����Ǻܵ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ѱ�����ߺ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�ֻ�ܳ䮔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µġ��~�塱�����ܡ���(d��ng)�桱�ĕr�����t��ɽ��Ȼ�؈�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ƶY�����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⡰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^�v���e�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ɾ�Ԋ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Ř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ʷ�϶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ȫ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bi��o)�e�ġ��Y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�Ǻ��傃��(qi��ng)���r(n��ng)�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ģʽ���ɞ顶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鱾�ĕ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·��Ҫ�ǰl(f��)չ�r(n��ng)�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v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(q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ǂ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t��ɽ�f����Ԫ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Ɯ������sȫȻ�����ƶ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B�⳯Ҋ�r��С�fͨ�^�ʵ�֮����Ҳ�ѡ�ʿ�����δҊ���жY�������鮔(d��ng)���ăɴ���֮һ���ڶY��ʽ֮�r���t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ʥ�^�^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QӋ��P(y��ng)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
�҂��@�Ͼ����Ž��һ���t���Dž�̩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s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һ��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٣��ùŶY�Ř��¼�����˴����(x��)�W(xu��)�Y�����ɾͳ�Щ�˲���Ҳ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x��)�W(xu��)�Y�����ɾ��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ҡ�����ԶY���ĶY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҃�(n��i)��ʥ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˼·��
��ҵ�ʥ���t�˶�úܣ��ιʪ�(d��)��(d��)̧��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ط��Ե�ԭ��֮�����Ƿ�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̫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^���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Ȼ������λ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Q֪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ܼ��v֮�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Ӻһ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o�aһ���ąǵ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?sh��)��?x��)�ה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λ�o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ɶY�Ŀ�ģ���ɞ����жY�ε�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켶����G�U���Џ����H���c(di��n)�S���ӻ�ɽ�ǘӹŴ����˵��L(f��ng)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ӵ��t�˸����υ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f�r�u�c(di��n)�ҷQ�顰���е�һ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ݲ�ʿ�����ġ��塱ζҲ�Ѳ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ћ_�����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»ݣ��¶��վ���(ji��)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d���ģ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Ҳ��Ը��λ�������Ⱥ��ӵ��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̩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»݈Գ֡�ֱ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IJ��Q���Ļݡ������ǹŴ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՜Y���Ǖ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Ԋ�ˣ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ڵĹ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у�(n��i)�ڵ��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ݲ�ʿ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Ļ��A(ch��)�ϣ��Էdz�ƽ��(sh��)�ĹP�{(di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ʵؔ����ݲ�ʿƽ���ò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Ľ�(j��ng)�v�����õĶ��ǘO���̵�����䣺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ˌ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Ȣ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˃��ꡱ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ꡱ���P�{(di��o)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һ��혺���Ȼ�Ě�퍡����f��•�³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(n��i)�đ�(y��ng)����̓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_(d��)ؚ�����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ı�Ȼ���\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ݲ�ʿ�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̕������X�B(y��ng)�Һ������]�^���ˣ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(di��n)�X��Ҳ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ڵ��ζ��µĖ|���c��(n��i)�ڵ��ζ��ϵĖ|�����\�����I(y��)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ֵ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ʿ���e����qƫ����˶��و���o(j��)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j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50�q����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٣���Ҳ�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]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٣����@ʾ�Լ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ش������e�]���Ǜ]Ʒ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һ���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ʹ��Ū�������Tа����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Ԋ������̹Ȼ�ظ��V�ˡ���߀մ���Ĺ⡱�������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\��֮�A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ٮ�(d��ng)���\�����ֶ����@�ѽ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˶������[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ѵ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ţ��挍(sh��)��ɫ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Α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ۣ����@���ڳ�Ó���A(ch��)�ϵľ����䐂���@�ѽ�(j��ng)�ܽӽ��ڵ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ı�ֶ��ס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ݲ���׃�u����߀Ҫ������Ҫ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Ӛ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ɽo��ֶ���ݡ������O(j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ף�������̎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Ł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Ʋ��J(r��n)�ã��f���]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ҏġ����º͵»��Ƕ�ٝ�S�@��Џ����ڵ��ҵ��˸���Ҳ���Ժ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ϡ���ͬ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Ąt������Ó���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ӌ�韟o�H���ݼ{һ�м�(x��)����һ�Љm�������и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(t��i)����(y��u)�����g��ֻ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��ӌ��ȽY(ji��)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P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քe�IJ�ͬ�ĽǶȁ����չ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е��DZ���ͻ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f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@ʾҪ�v����֮̎�����t��ɽ�����@ʾҪ���ƶY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ݲ�ʿ�����@ʾ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혺���Ȼ����ô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@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ӳ�Ó�đB(t��i)����
��ʿ�a(ch��n)���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ӛ•�������Ƹ��ʿ���Y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衳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ؑ�������g(sh��)ͨ�������߲��ó����[�Ӳ���λ��Ҳ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в��e�ƶ����ɡ��l(xi��ng)�e���x���]�e�x�ι�������(bi��o)���Ե��О��(bi��o)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]�e���٣��ز����u(y��)���ʷ����Ե����߱�ȫ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إ��ʷ��ӛ�����塰�|�h������(ji��)���l���c֮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ٝ�S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u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ٵĽݏ������Ǻ���֮�L(f��ng)��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(y��ng)�\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(y��ng)���B(y��ng)�u(y��)��Ψ�������ȶ࣬�����I̓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ʿҲ�ͳɞ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ӳ����F��
�����Խ���Ҫ��(sh��)�п��e�ƶȣ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]�e�����ٵ��k��һֱ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峯�y(t��ng)���߸��Ǽ��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ѝh����Т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ɿƺϲ���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Ӻ��Ԫ�꣨1723�꣩�t������ط��C(j��)��(g��u)�M(j��n)���]�e���n��Ʒ�����ã��Ժ�ÿ���ʵۼ�λ���]�eһ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͵ط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ӡ����١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��f�B����Ǒ�(y��ng)���ٵ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_ʼ�O(sh��)���R�r�Ե��ƿƣ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θ����Ժ��O(sh��)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O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꣨1679�꣩��Ǭ¡Ԫ�꣨1736�꣩���ɴ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w��ng)�_�ͻ\�j(lu��)���u(y��)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Ǿ����Լ�Ǭ¡Ԫ����ܵ��]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(j��ng)�v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ڰ˹ɿ��e�ƶ��У�Ҳ��ؕ�e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u)�еȺ����]�e���ص���Ŀ���ﳬ�˱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}�˃�(y��u)����ؕ��̫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R��Ҳ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}�˃�(y��u)�����f�Е��wĽ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@һ�M(j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ǂ������Ľݏ�������Ҋ����ȡʿ�@�l·����ʹ�ڌ�(sh��)�а˹�ȡʿ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]���Д��^���@�͞�����ɫɫ����ʿ�ṩ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Ҳ�̼����T�l(f��)���廨���T�ļ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ǻ���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̓�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@�l���K�Ͻݏ������\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߄t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£��̈́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qu��n)�T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e���Ǿ����茑��һ��һ�ѵļ���ʿȺ�w���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Ӟ�ʳ���ĺ����LÖ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wѩ�S����õ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Ͼ�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L(f��ng)�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Ц������ӹ�ןo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
�Ǿ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ʿ�Vϵ�������ݵ�κ�x��ʿ����˼��YԴ���Բ錤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[ʿ֮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6��499퓣�����˼��Č�(sh��)�H�����ǽ��˔[Ó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Ŀ��]�����_(d��)��һ�N��Į���o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ڲ�����Ļ�Ը�c�y(t��ng)���ߺ�����ʿ�ˣ��ṩ��һ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Ȼ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ʧ֮�ϣ���ô�˾��ܱ����Լ��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ۣ��^���ڱ���֮�T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f��֮�ϣ��ڳ�Ó�Ļ��A(ch��)�ϫ@�þ�������ɺ��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Ė|�����繦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縯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Ȼ�͌�(d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[�ݲ�������ŗ�������Ę�(bi��o)־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ĵȣ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@�N�����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ϵ�һ�N�{(di��o)��(ji��)���a(b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t�Ǿ������ɵ�һ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S���hĩ����ľ�׃����κ�x�r��W(xu��)�Ī�(d��)���λ�l(f��)���ӓu��ʿ�Ă��w�˸����R���µ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ǷN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ּ�⣬���c���Ծ㻯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m�Զ����b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ʿ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_(d��)�ľ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e��κ�x��ʿ���瘷֮��(x��)����Մ֮����ɽˮ֮�d����ˇ֮Ȥ���B(y��ng)��֮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֮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МYԴ�P(gu��n)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]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˼�뿹�����̣���ָ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ף�Ŀ�v�Q����ߡ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•���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z���(bi��o)�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r����څ�ε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κ�x�L(f��ng)�ȏĴ˱�ɞ�v����ԸѭҎ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ҾV�o(j��)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Ľ��һ�N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@�ӵ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澫�����⽨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`��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ɞ�⽨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һ���M�ɲ��֡����t�lj�����2�����eһ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һ���S���ǂ��f�е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[���^��ľ����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κ�x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�e���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ף�������@Щ����㣗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(d��)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ѩ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^(q��)�e�_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?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ό����ͳɞ顰��ʿ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͔�ʡ���ӹ���(q��)���{�S����һ��Ԓ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߷⽨��·�����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ڲ�ѩ�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ʎ�ڿ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顱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Լ�Ҳ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H���Ծ����@һ����?zh��n)��y(t��ng)֮�С��o��(d��)��ż���Ȳ�ѩ������ąǾ���Ҳ�A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κ�x��ʿ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_(d��)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Ͼ��r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F;�����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ػ�ˮͤ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f�����팢�[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Ѿ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Ȫ���ݲ�ʿ��ԭ�ͣ�(li��n)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Ҋ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IJ��ü�����һֱ���R��ǰһ���꣬���}ԁ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_�r�����뵽��߀�ǣ����P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֮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Ľ�@��λ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ȫԊ����ּ�������ȃɾ��ˣ�ǧ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꾰��D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ȭȭ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κ�x�L(f��ng)�ȵ�Ӱ푝B�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Ʒ�У��e�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ԭ�͵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�ľ���֮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N������Ʒ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в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(d��)���˸����ʿ��Ҳ��Ը��ͬ���͛]��ӹ�����ĝh�x��ʿ���γ�һ�N�^��и���֮ʿ�خ�(d��ng)�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֮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)�г��~��ӹ�����ǘ�(bi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ɞ���ʿ�Ă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^���@�N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Ǿ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c��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˷Q�����ˡ��t��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Թż����y�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ɗ���м������(w��)�����ڵĹ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v���ݵ��L(f��ng)ò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ڵIJ��ԣ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v����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��Ȥ����ӳ�˂��w�˸���X�Ѻ�����
�Ǿ����ѡ��Xؔɢ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䡰ƽ�Ӻ��e���팑�������Ó�ף��z�����(w��)�����Xؔ�ֳ�Ó�Ğt���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ӝ�(j��)�˕r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䌍(sh��)��Щ��֮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Ƕ�������м��һ��أ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S��һ�Ӵ�l(f��)�Xؔ���lҪ�l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迼�����t�Ƿ��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Ó�������۵���ʿ�L(f��ng)�ȡ����Ȳ�����ڸ��F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v����ؔɢ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ʳ�����ﵭȻ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@��һ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κ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ڿv����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κ�x�L(f��ng)�ȱ��F(xi��n)�ΑB(t��i)�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Խ�ŵ�����˼��ɷ�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՚���һ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]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ٮ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ߘs�u(y��)�����s�ԛQ�x�^��Ѳ����]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¹֮�ԣ���Ұ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뷽�O(sh��)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f���Ĵ�Ҫ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Լ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ֱ����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Ȕ[Ó���Xؔ�ׄ�(w��)���b�O���֛_�ư˹��e�I(y��)���λ\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挍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ӆ�����ʲô�b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Ͼ��@�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ڼ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Ծ����ò�������ôҪ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Ͼ�����Щ�Լ����¡���߀��Ҫ��һ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M��ª�Ą��^���С����[Ҧ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ӵ��֡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߅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Ц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v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·���ڮ�(d��ng)�r�@�_���@����Ď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ζ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خ��О�ð�^���ǂ��r����֮�Ѿõ�ԭ�tҎ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Ū��ӹ�����ձ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ˡ��ā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ڌ�ijЩ�⽨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ͷ⽨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đ�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x��(j��ng)�ѵ��Ŀ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䌦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עጱ��J�����(bi��o)��(zh��n)�𰸵ĕ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ͦ���fֻ����ע�ǡ���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Ԋ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䳪���{(di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ġ�Ԋ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䢡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Ԕ�֮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䢡�֮Ԋ��Ҳֻ�Ƿ�D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c(di��n)С�ČW(xu��)��ʽ�Ą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W(xu��)�̗l�����l(w��i)�Լ����О鷽ʽ�����_(d��)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Ի�u�Q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һ�N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Ȼ�Ԙ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Ă��ԣ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e�˵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ᵽ�ػ��ӷ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ە����龰���ͺ������ɷ����Ě�գ������ӷ����Ӵ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ɢ������{�ڿ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Մ�����(j��)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˵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˽���Ҳ���H��ƽ�ȵ�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g�˽����Ϡ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Ϡ��Ծ������T�͊䟨�ġ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ڡ��H�Է�����ƽ�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ċDŮ�^Ҳ�^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{��L(f��ng)֮��ⱺܲ��M�⡣��֦���ʞ�����ӵ��Ͼ������\��Ӌ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桱�����Ҳ�f�����桱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ɲ��⡣������Ҳ�Q���顰ϣ��Ŀ͡����s�J(r��n)�顰�ɾ��ĘO�ˡ�����Ҋ���dz��ڑz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أ�ٝ�P(y��ng)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ɫ�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ҕ���F���A����η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Ū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ϧ���ʡ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֮�g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һ߅����Ó�ĸ��{(di��o)��һ߅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ѣ������Ϟ�Ó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Ԏ��п��Q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ɫ�{(di��o)��¶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ĵđ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ʹ������ʿ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˲��M�⽨�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Ǐ�(qi��ng)�ҵIJ��M���܉�����r�µı��l(f��)�ΑB(t��i)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�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߱���һ�ӡ���(d��)���r��ʿ��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|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һ�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ū�����ݱ����Մ�e�I(y��)�ĺ�̎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u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˼Ҟ��ӌO�l(f��)���l(f��)�FҪ�Һ��L(f��ng)ˮ�w���ڵĉ�?z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w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ӌO�\���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˷N�N��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P�e���ñ���33�ؿ��u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Ҋ����
�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еąǾ���Ҳ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ƺ�����ÿ��С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Ρ�����Ҋ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о��Y�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żȻ�ģ���ѩ��Ҳ�Q���Đ۵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|�ϵ^(q��)���ڳ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x��ѿ�����н�(j��ng)��(j��)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˵Ļ����ؔU(k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۽��_�����˼��Ҳ�^���S����Ը�ܷ⽨�s���IJ��Ӽ�����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ɫ�ʵġ�ǰ����ѩ���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ף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쵝��ϷQ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ͱ�ҕ�顰���ݲ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߭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ҕ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�߭��ԷQ�����ء�����Ը�鸻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⚢������μ��ҕ����ˣ���(d��ng)?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ֶ����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ӷš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ͬ�Ӳ��Ϟ顰���°���֮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ĕ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`���Ա��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˪�(d��)�صĄ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Ժͪ�(d��)��(chu��ng)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r�����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Щ�˘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ڡ����鷴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ˡ��V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κ�x��ʿ�ѽ�(j��ng)ǰ�M(j��n)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�˕r��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С�fĩβ���ˡ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Ѳ�ˇ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֡����όW(xu��)���˵ķ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Լ�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ĸ��{(di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Ԍ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߅������ҕ������Ո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ĸ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Ը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ۃ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ʩ�l(xi��ng)��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Ę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Ǻε�֮�ˣ��ҁ����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ֲ�؝����X���ֲ�Ľ��Ąݣ��ֲ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ҽ��Ҍ����ց�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һ�NŤ���ķ����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䡢�Z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̶Ȳ�ͬ�طքe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ĕr��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һЩ�c����h(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)�{(di��o)����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Ը�һֱ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Ѹ߀�ј�(bi��o)־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Q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Ʒ�Q�顶������ӛ������Ȼ�ԡ������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ݵ���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Ų���żȻ�İ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f�B��ӵ�����ּ֮�������͕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cɽ���[�ݲ�ͬ����Ȼ��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Y�ǰ����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ҵ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Ǟ��`����ҳ�֮̎��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o��߀�ң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ҲҪ���ûʵ۵ġ�����߀ɽ��ּ��ņ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{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֮�Y���У��ԷQ����¹֮������Ұ�T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Լ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ð�۾�֮��b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ҏĴ��B��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ٲ����ӿ��e�ĸ��ԇ���ɗ��˹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ؼ�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x�˿��e���Һͷ⽨�A������Ҏ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ߺ���ҕ�����żҵ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t�˵ă�ֻ�_߀վ����҂��y(t��ng)�ķ��h֮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˅s����һֻ�_�����҂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c�⽨�h(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)�{(di��o)�Į��˃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t�˵Ļ���в��^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ͻ����ٌ��⽨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ĺ��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ߺ��־���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߲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ꡰ���ɌW(xu��)���L�Ńx�������ð��@����̥�˜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t��ɽ�f�ģ��ߺ��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ݡ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C���@Щ�����ߴ�ʹ�˷⽨�A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x�˷⽨��Ҏ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x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Ҳҧ������ҵ�Ě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f�B�⡢�t��ɽ���ݲ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e�O���c��̩���ĶY��ʢ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Ⱥ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ʿ�ij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ǻ��a(b��)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ʿ�ij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˶��@�Ü��ś_������ij�N���x���f����С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(b��)�f(xi��)�{(di��o)���Ї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Ļ���څ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顰�[��ȫ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ǡ������ϓ����a(b��)�Įa(c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ʿ�ľ���Ʒ����
���ᡰ���M��ʮ�q���Ͱ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ʷ�ϵĴ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oһ��؞ͨ�����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Ҫ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֪�R������Ψ��Ҋ���R�V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ܔXȡ��N˼���Ļ��B(y��ng)����ȥ�Ƴ����d�ǻۡ��İ˹ɵĶ������ɞ�Գ��Լ��ġ����г�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)���ݲ�ʿ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Ƚ��д˷N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Ҳ�ǷQ���t���Q���桱����Ҫ�l�����T�߿h֪�h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k��Ҋ���ᣬ�����o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Ҟ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Ϡ���Ʊ�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Ո��ԭ�Dz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˼�ˣ��Ҳ�Ըȥ���Ϡ�Ҳ������Տ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ôԒ��Ʊ�ӂ�����Ҫȥ������Ո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@���Dz��Ŗ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ɽ�Գ��u�r�f�����˵��fԒ��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֪�h�в������o�ֵ��I�k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ɽ���ڡ�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ۣ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Ҋ֮���t����Ҋ֮������Ԓ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•�f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͵ر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t˼����t���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飬��λ�߱�횎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H�Ե��T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ɴ�ģ��ӵ����t�ˁ�Ҋ�Լ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أ��t��(y��ng)��(d��ng)�ܽ^�@�N��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²�Ф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t�˵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²�Ф֮�������Բ��t��֮�����t�ˡ������ǽ^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Ҋ�t�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֮�TҲ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ܽ^�r֪�h����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N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@�ﲻ�H�ǡ������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(y��ng)ԓ���ܵ��ن�֮�Y�Ͳ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t�²�Ф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�ȥ ����ŰС�ġ���Ф��֪�h֮�������ľܽ^��څ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˸�ı��F(xi��n)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•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¡��^�m(x��)�l(f��)�]�@�N˼�룺����ԭ��(zh��n)�䳯Ҋ�R����һ �f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Ҋ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ȥ�ˡ�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\�ɣ��t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c�О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P(gu��n)ϵ�硰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ڹ��١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W(xu��)�ɶ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ô���Ƿ��nj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Ի�����R�˟o�����x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ҷLj�˴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R��Ī���Ҿ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ܽ^�r֪�h֮�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Ԫ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͡������x�c���ԡ����@ͬ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ߡ�����Ԫ谮�(d��ng)�ʵۺ������Ƹ�����s�B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t���ֶ����[�ݸ�ʿ�ijɷ����˂��Բ�����ӛ�ǂ��ա����o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ԭ�¹ڣ����˸�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ţ܇�d��ĸ�H������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߅����̎��ˣ���ǵ��l(xi��ng)�º��ӂ�?n��i)����Ⱥ������Ц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t���˸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ʿ�L(f��ng)퍾��@���څ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�ľ���֮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c��Ȼ�|(zh��)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˺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c��Ȼ���C���ڵľ��硣�������ϵĺ����ɫ��ұ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`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܌W(xu��)���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x����І���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茑����(x��)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Ȼ�Ě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εΣ����~��ˮ��L��Lȥ���ĺɻ������H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Ⱦ�ĸߝ��˸�Č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ͨ�ľ�ɫ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ô��Ȼ�����ţ��ֳ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`�ӵ���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Ȥ�ķ������@�N�⾳�@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c��Ȼ���ڵĮ�����_(d��)�����Ѳ��H��һ�N�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ȫ�˵Ĵ��汾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(d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ٸ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a(b��)�f(xi��)�{(di��o)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ߌ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O(sh��)Ӌ������С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ɫ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ö����ˇ@ϧ����ϼ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䡱�Ă�����һƬ���۵���ˮ֮�О��Լ��ٵ�һ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|(zh��)��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߶Ȍ��ȳ�ª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ğ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xӳ��Ҳ�Bӡ������к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߾����@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ֵ����c(di��n)��һ�治��ؔ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˸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־õğ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Ҳ��M�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Ƴ��h(yu��n)�Ŵ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κ�x��ʿҲ����ȻՓ�ĽǶ���֎���h(y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˺��C��̎���o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֮��ˮһ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@�ӵ����H�P(gu��n)ϵ���茑��һЩ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Ěw�淵���Ұ�ϣ����ό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֮�g���\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⌍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b���_С��Ϟ���ţ�σ��c�_С��IJ��ϵ����ַ�֮�g�~ˮ�������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ߌ�����֮�g�\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ֱ�����桭�����˶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㵭�h(y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͘㌍(sh��)�غ��Ʒ�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M�M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鹝(ji��)�ƺ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٣��䌍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ЙC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鹝(ji��)���İ��H���ȵĽY(ji��)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҂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Ǿ������ڌ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\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Ěvʷ��˼��ͨ�^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(ji��)��(g��u)��һ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ɣ��M(j��n)�д�đ�ēP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ؽ�ʾ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º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Ю�(d��ng)Ȼ�����ˌ��˹ɿ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ͬ�r���J(r��n)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(ji��)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Ѓrֵ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����Һ͵��ң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្���µ�Ԫ���Ը���ʿ�ֵ�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(g��u)�µ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һ�����Ŭ���mȻ�ܵ��v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҂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R�кܴ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齨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`�������̽���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h(yu��n)ֵ���҂��羴������h�








�l(f��)���uՓ �uՓ (0 ���uՓ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