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ˇՓ���о�] ԭ��(chu��ng) �����y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c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Փ�Z��ɡ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c���˼��Y(ji��)�ϵ��U��
��6 ���� 386 ����x 2024-07-06 09:07![�����]](image/app/3.gif)
ԭ��(chu��ng) �����y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c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Փ�Z��ɡ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c���˼��Y(ji��)�ϵ��U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һλ��Ҫ�Ľ�(j��ng)�W(xu��)�Һ��܌W(xu��)�ң�����κ�x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̈́�(chu��ng)ʼ��֮һ������ؕ�I���ڄ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Փ�w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ˏĝh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W(xu��)��κ�x���W(xu��)�Ą��r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ע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Փ�Z��ɡ��ȡ�
��Փ�Z��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Փ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ԏ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{(di��o)�ˡ��o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Դ˞���A(c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ͽ�ጾ��w�ĵ��º͂��톖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N˼�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Ƴ硣
������Փ�Z��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κ�x���W(xu��)�еĵ�λ����ӹ���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Փ�Z��ɡ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չ�_�ˌ��Y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ӑՓ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䡶����ע���͡�����ע����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ɵı����h(hu��n)��(ji��)��ʹ�F�oՓ�܌W(xu��)�γ���һ���A�M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䱾�wՓ�܌W(xu��)���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Փ�I(l��ng)�顮�����c��Ȼ���@һ���W(xu��)�r���n�}������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㣺������<Փ�Z���>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1993���5������95퓣��@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ں���ʥ�˟o��Փ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ڡ�Փ�Z��ɡ�Մ?w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ԡ��͡��顱���}��
�����ġ�Փ�Z��ɡ���һ����Ҫ���܌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c���˼��Y(ji��)�ϵ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o�Οo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˂�ֻ��ͨ�^���ص�ֱ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N�^�c���ں�����κ�x��ʿ�a(c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˼�����뵽���˼���У��Դˁ폛�a���˼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״���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Փ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һ���Ȕ�(sh��)�N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O�ߣ���M�˄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Ե�Ҋ����
���ā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Փ�Z��ɡ����҂��ṩ��κ�x�r�ڵ�һ�N��Ҫ�܌W(xu��)˼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Փ�͌����˼���ԏ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ǂ��r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Փ�Z���⡷��ע�⡰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ь��TՄ���ˡ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ɵö�Ҳ������Փ�Z����ұ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ע�ƣ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Ԫ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ʲ��ɵö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̡�Փ�Z���⡷����٩��Փ�Z�x�衷ע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̌����ԡ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؝h�����m�p�ڬF(xi��n)��硰�ԡ����Ɛ������ٸ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߶���u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κ�x�Է��f��ǰ�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Փ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ԡ��Ľ��x��ͬ�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ĸ��N��Ȼ���ܵĻ��翂�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ǟo�����Z�Խ�ጵ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Q֮�顮��Ȼ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㣺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Ͼ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1996��棬��323��324퓣��@�ͺ��̌����ԡ��Ľ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˃ɝh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ϵ��һ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̽ӑ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漆�r���҂��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ğo�M�ǻۺ�δ��֮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Խ�(j��ng)���ҕ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еĸ߾S�ǻ��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̎��ϴ�����@һ�^��Ҫ���˂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ĵ�ƽ�o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\�з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
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H��һ���܌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ָ��(d��o)�˂�?n��i)���ڬ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Q�ߵ��Ļ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{(di��o)���t̓���غ����wՏ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̌�(d��o)�˂��ڱ��o�Լ���ͬ�r��ҲҪ�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͎������˵�Ʒ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߀�漰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J��ü���ܷ�ӳ��һ���˵��Ը����|(zh��)�͝��ڵ��\�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~ü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N�͜��ᣬ����韵�ü�g�t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˵����؏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չ���ǣ����̌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ˁ턝��ʥ���˴˸��x�����˟o����Խʥ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ں��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ŭ�`����Y�ε���ŭ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̡�Փ�Z���⡷����٩��Փ�Z�x�衷ע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־•κ������ӛ�d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̣��Ԟ�ʥ�˟oϲ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ꐉ�������֮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־����28��κ����犕�����ע����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1982�������795퓣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֮����ʥ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δ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鮔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δ�L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ͮ����κ�x���W(xu��)Փ�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957��棬��74퓣�ʥ�ˡ��c��غϵ����c�ε�ͬ�w����ͬ�ϣ���73퓣������̵��@�N��?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ʥ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Զ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ʹ�ú����F���o��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Փ�ϳ��F(xi��n)��ȱ�ݡ������Զ��o��tʧ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^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s�ڴ˻��A(c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�ֻ��ʥ���ǻ��Ԃ���ܡ��w��֮ȫ���ԟo���ġ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79퓣������Jʥ���ǡ��w���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汾�w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˸�ͬ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̵�ʥ�˟o���f���Ը��죬ʹ���̵�ʥ�˟o���f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�ʥ�����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Մ����ʥ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P(gu��n)ϵ��
�P(gu��n)�ڷ����c�t�ˡ������顱����ʥ�ˡ����Ї��܌W(xu��)�Ěvʷ��һֱ���˂�������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c�h���T�嶼�IJ�ͬ�ĽǶ�̽ӑ��ʥ�����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(n��i)�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κ�x֮�r����ʿ���r����ՄƷ�}���Ҳ���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ò��̽ӑ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錦�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ʥ�˵��P(gu��n)ע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ʥ�������̽ӑ�ɞ��ˮ�(d��ng)�rһ����Ҫ�Ć��}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Է֞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ʥ�˟o�飬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۵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ӛ�d�ˮ�(d��ng)�r�T����ʿ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}�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Ԟ�ʥ�˟oϲ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Փ������犕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c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Ȼ�׳���ʼ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ߌ��ڱ����}�^�c����һ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ʥ�˟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Part.1 ��Ҫ�^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܌W(xu��)ʷ�ϘO����Ҫ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Փ�����\�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ԟo�鱾�����F�oՓ˼�붼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r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ش��Ӱ���ͬ�r߀��(y��ng)ԓע�����߀��һ����Ҫ��˼�룬�Ǿ��ǡ�ʥ�����顱��
�cʥ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ʥ�˟o�飬�@Ҳ�Ǖr�����J�ɵ��^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Ԟ飺ʥ�ˡ��oϲ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ᘌ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W(xu��)��˼����Ҋ��ԇ�D�ı��wՓ�ĽǶȁ��oʥ�������¶��x�����J��ʥ�˳���֮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ڟo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ڟo���ʥ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أ��m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ϟ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ʥ�˟o�����Ҫ��һ���^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鐺��ʥ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А�֮�飬ʥ�˟o��Փ��˶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Z����ӛ�d���@��һ���r��̽ӑʥ�˟o��Ĺ��£���ɮ�����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ƈ�Ӂ����c���Z����ʹ�䳪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Ի����ʥ�����鲻������Ի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؆�Ի����ʥ������а������Ի�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m�o�����\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ɮ���ƣ����l�\ʥ��а����ƈ�Ӳ��ô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Կ���ʥ�˟o�錧(d��o)���ˮ�(d��ng)�r�е���ʿ��ʥ�˿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rҲ�y�Իش��l�\ʥ��а�����Ć��}��
����ᘌ��ڡ�ʥ�˟o�顱������ˡ�ʥ�����顱����ʥ�����顱�@�����}�䌍���ڱ��_ʥ�˵����g�ԣ���ָʥ���ھ��г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|(zh��)֮�⣬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ƻ���ͬ�ĵط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ڌ�ʥ�˵���Ʒ��Ĕ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ʥ���˸��̽ӑ�t����ȱ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@��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飺��ʥ��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ï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_����ͨ�o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ʲ��ܟo�����ԑ�(y��ng)����Ȼ�t��ʥ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ng)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ʥ������Փ�Ѓɂ���Ҫ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һ�ǡ�ʥ�����顱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(y��ng)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ԏı��wՓ�ĽǶ��M��Փ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(x��)�����ӌ������wՓ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_ָ�������ԟo�Οo��ʼ���f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ڵ�ʼ�����ɣ������顱��ȻҲ���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ɵ�����֮һ��ͬ�r������ע�⡶���ӡ��r�֏��{(di��o)ʥ�ˡ��c��ϵ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ͨ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ڸF�O̓�oҲ���F�O̓�o���õ�֮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ڲ��F�OҲ����ʥ���܉��_�����c��ϵ¡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ȻҲ�܉��w�ڴ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f����Ȼ���顱�˵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ʥ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ͮ�����J�飺���w�o��Փ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Ԅ��o��֮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ǏĄ��o�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醖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а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ʥ�˵ı�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՟o֮�����܉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׃����׃�����ʶ��܉�a(ch��n)��ϲŭ�����ĸ��顣
ʥ���c���˶�����ϲ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ʥ������֮̎���ڡ���(y��ng)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ʥ���ܵ����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mȻ���߂䳣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ܵ�����Ġ��B����ôʥ�˺��ԑ�(y��ng)�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K���ʷ��Ӽ����`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Ƅ������m�Ӆs������֮�o���@Ҳ���njW(xu��)���ձ��Jͬ�ġ������顱���^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顱���^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Փ�Z��ɡ�������ע�Փ�Z�С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(x��)���hҲ���r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飬���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Ҳ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ʎʧ�棬������֮а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Է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ġ��Խ��顱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鿿�n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(x��)����ô�W(xu��)��(x��)�ă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߂���Ȼ�Č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ڵ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һ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߂�ľ�����Ȼ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ӛ�d������ע��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ו��ԑ�֮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Ԍ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Ȼ֮�ԡ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A(y��)����Ȼ��֮���ܟo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ܟo�����ֳ��M˹�ˣ��Ԟ�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Ȼ֮���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m�Ѷ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(n��i)��Ȼ����Ѯ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֮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Ḹ֮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ԟo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Փ�ǿ�ʥ��߀��ض����a(ch��n)��ϲ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鱾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Ȼ���ߵ����ԛQ�����ٶ��˞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ܸ�������ʼ�ʹ������ʥ�˿���Ҳ��Ȼ���顣Ԭ��ϲ�ώ��J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܌W(xu��)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̏��P�ġ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ı��w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˞鱾�������ڌ����˵���Ȼ���Ե��Jͬ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ֻ���ɞ�һ�Nʧ�s�˸��`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ġ����h֮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ܵ���
����ʹ�á�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ʥ�˵ă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ʥ�˾߂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_����ͨ�o����ʥ�˵ľ�����ƽ�o����Ҳ�c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܉��J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;�m�����wͬҲ���]�m�ٶ�����һҲ����Ҏ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ʶ��܉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뻣�Ҋ�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ʥ���mȻ���ǻ��Ԃ䡱���г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ͬ�ġ���Ȼ֮�ԡ������c�鶼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nj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ʥ�˄t�����Ԟ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й�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ʶ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ԣ�ʹ�鱣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܉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ܵ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鲻��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��(ji��)֮������협�(y��ng)��Ȼ��
Part.2 ̽�P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^��ľ�����֣��κΌW(xu��)�f˼�붼�����܉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c֮���P(gu��n)�ČW(xu��)�f����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Ȼ���c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(li��n)�ČW(xu��)�f�ǡ�ʥ���w�o����
���^�ġ�ʥ���w�o������ָ�ھ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ڡ��o��ͬ�w�ľ��硣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ʥ�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ǻۡ��@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ǻ۲������܉�ĺ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(x��)�c���`�еõ���ʥ��Ҳ�܉��\���@�N�ǻہ��w�����w�ġ��o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ʷ��ӛ�d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@һ���}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ȥ���L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ʥ���w�o�����}��ʷ��ӛ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՞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δ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Ҋ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Ի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\�f��֮���YҲ��Ȼʥ��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֮�o���ߺ�������Ի����ʥ���w�o���o�ֲ�����Ӗ(x��n)���ʲ��f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ʺ��ԟ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Փ���o�r���J�顰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ʼ���ԟo�鱾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־߂䡰�o�Οo�����f��֮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w�o֮�w�����H�Ͼ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o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Ԃ����ʶ����˲����w�o��ֻ�о߂��ǻ۵�ʥ�˷����w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ʥ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܉��w�o�����ܳ�ʥ������̎�ڡ��С����s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o���ʶ��ȿ��Ӳ�һ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ԭ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ܵ��˝h���ԁ���W(xu��)�Ļ���Ѭ�գ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κ�x��ʿ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Կ��Ӟ�ʥ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o���˼��O���Ƴ�����ô��Q��Ψһ�������nj����ҵ���Ȼ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ʥ�˵�Ʒ��֮����ʹ֮���Ϟ�һ���@�Ӽȷ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Ѭ�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(y��ng)���ܵ���Ӱ푵ăr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ԇ��Q�����c��Ȼ�@��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Ŭ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{(di��o)ʥ�ˡ��c��غϵ������ܰ�֮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Ω�o��o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غϵ¡���Ҳ����(y��ng)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һ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Ͼ���ʥ���w�o���ԟo������ʥ���܉��c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Б�(y��ng)���܉ֿ՟o�o����K���ľ��M�뵽��Ȼ�Ġ�B(t��i)����Ȼ�܉�ֱ���w�J���w֮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ɡ����@��Ϳ���(li��n)�뵽������Փ��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Part.3 ֪��֪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ʥ���^�^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ֻҪ����ס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c����Ȼ���@�ɂ��P(gu��n)�I����Ϳ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Ξ�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Ξ�ʥ���w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ʥ���^����һ�ܘ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ʥ�����߂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g�ԣ�ʹ��ʥ�˲����dz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߂��˾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Nʥ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ڵ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ǃ�(n��i)�ڵ��˸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ֵ��ע��ĵط����M�ܱ�֪�R�c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܌��˵����p�ģ��Ԟ�ֻ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ڷ�ֵ�^�͵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㽭��W(xu��)��2023���оͿ����^�P(gu��n)��ʥ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}���ʶ���Ҫ��ҕ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á����f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š��е�һ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犣�������݅����ϣ���ڟ����Ă俼�c���s�Ĭ����в�Ҫ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ĥ���M��ϣ���܉��^�m(x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ğ�ۡ����Ͱ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܉�ɹ��ϰ���
ʥ��֮�����ʥ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n��i)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ھ���ʥ�˟o�茣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һ��ʼ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ʥ�����µ��t���cС�˶��衰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ס��R�ԡ�����ע��ՈҊ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ጡ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1980�������312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顱��ص��t�˱���r����ʡ�����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˅s���ĺ���ʎʧ�桱���Ρ���֮а�����oՓʥ����߀���t�ˡ����˰��գ�����Փ�϶���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顱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һ��ֻ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顱������߶����ǬF(xi��n)��֮��Ȼ�c��(y��ng)Ȼ����ʥ�˶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ь��@һ�������顱����֮��Ȼ�͑�(y��ng)Ȼ׃���ˬ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ʥ�˵ġ������顱�f���ף��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ʥ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ͮ����κ�x���W(xu��)Փ�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957�������98퓣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Զ����t��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ጡ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1980�������626퓣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С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С���֮а������ʥ��֮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֡�δ����á��ğo�Ɵ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۟o˽��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�o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˽���Ӷ����䳼�������̡�Փ�Z���⡷����٩��Փ�Z�x�衷ע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ʥ�����Զ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Ԑ��ˡ�����Ҳ�]��ʹ�䡰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ʥ��ͨ�h�]����(y��ng)׃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ܺ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Ա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ﲻ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ጡ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1980�������632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ǡ��Լ��顱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֮���ʹ�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ʹ�䡰�顱��(f��)�w�˵ı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ּ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а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633퓣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ֵ��ע�������ʥ�˵��@�N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֮�顱ֻ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o)���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Զ���(f��)�w�ڡ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ʮһ�¡�����ע��ՈҊ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ጡ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1980�������112퓣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Փ�Z���؛������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(x��)���h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̡�Փ�Z���⡷����٩��Փ�Z�x�衷ע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ڴ�̎����ע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ע�ĵĠ��h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Փ�����քeՈҊ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ʼ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1988��棬��387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㣺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Ͼ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1996�������322��323퓣���(f��)�ƣ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֮����Ҋ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ס��̡�����ע��ՈҊ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ጡ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1980�������374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ʥ�˷����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��Ȼ֮�ԡ�һ�c���サ�ӸБ�(y��ng)�͕���Ȼ��Ȼ�خa(ch��n)����ʥ��֮�顱,��ʥ��֮�顱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ǡ�ʥ��֮�ԡ����� ��ʥ��֮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c��ء��f��ı�����һ�µĶ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顱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)��

�����ġ�Փ�Z��ɡ���һ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ҽ�(j��ng)��ע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ͪ���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ǟo�Οo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Ͳ��ɸ�֪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ص�ֱ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N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Ȼ�^����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o�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q��)�ӵ����@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^�c����̎�ĕ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κ�x�r�ڵ��܌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ǂ��r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(ch��n)�����ͿƌW(xu��)���`�Įa(c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Ȼ�^����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o�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q��)�ӵ����@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ġ�Փ�Z��ɡ����H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ҽ�(j��ng)���ע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o�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q��)�ӵģ��@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N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܌W(xu��)˼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x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ʥ���С��顱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ʥ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Ԍ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ꐉ�������֮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־����28��κ����犕�����ע����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1982�������796퓣�����ʥ�ˮ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У����͑�(y��ng)Ҳ�Ќ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ʶ��䡰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ͬ�ϣ���795퓣������ڱ����Ϻ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ŭ����Ҳ�]��ʲô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̡�Փ�Z���⡷����٩��Փ�Z�x�衤̩������8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ע��֪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Ԓ���f�^����ʥ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̓�(n��i)�ھ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ڷ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ʥ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ʥ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̎���к͵Ġ�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ӡ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Ȼ�ؼ�����ȫ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eһ�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У�ʥ��֮�鱾�|(zh��)�Ͼ���ʥ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ʼ�K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K������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˰����ǘ���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ʥ��֮�錦ʥ��֮�Ե���Ȼ�⻯���s��ʧ���Ե�ͬ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c��غ���£��䷨���л������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Ӆs��˼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顢�����Զ��M�@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ጡ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1980�������631퓣��]�г�����Ƿ�؝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е�׃�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鲻�Ɍ������ǰl(f��)���˵���Ȼ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Ă��飩�����Բ����ԡ�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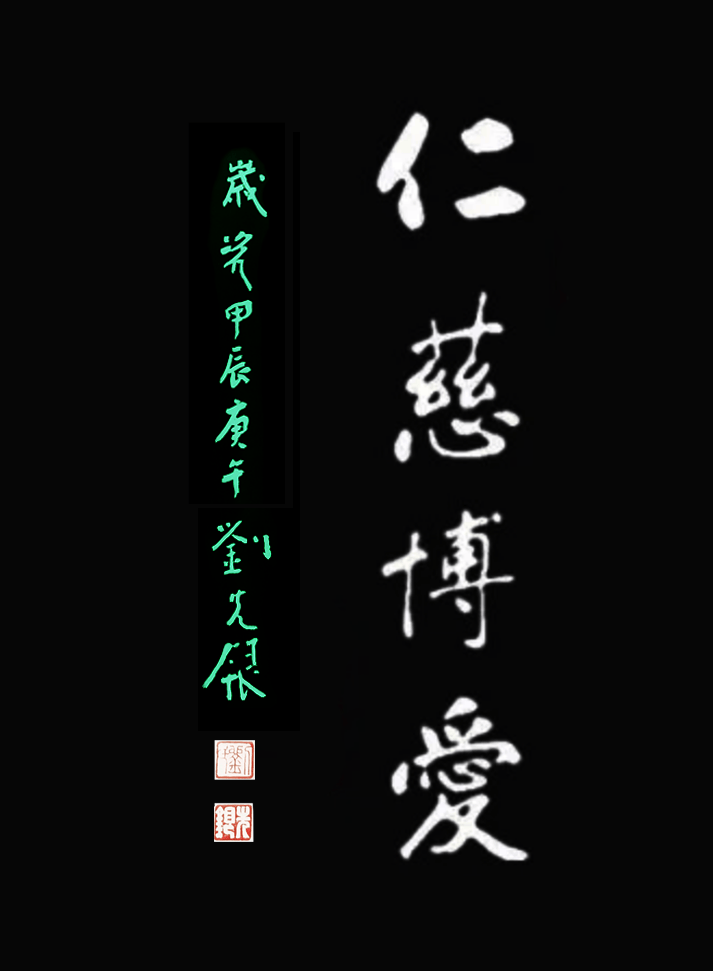









�l(f��)���uՓ �uՓ (5 ���uՓ)